发布时间:2025.07.03
源地址: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5-07-03/us-democracy-s-strengths-turned-out-to-be-weaknesses
美国的两党制长期以来被设计为防止极端主义的屏障,但如今,政治极化反而成为了助推剂。
美国人以其民主历史为傲,但对当前的民主状况并不自信:2024 年皮尤调查显示,72%的美国受访者认为他们的国家曾是世界效仿的良好典范,但只有 19%的人认为现在仍然如此。
发生了什么变化?
美国的政治机构依然完好无损,依然在运作。变化的是它们所处的环境:数十年来日益加剧的政治极化,使得原本被视为制度优势的坚固防线,变成了明显的弱点。那些专家曾认为能够防范反民主或极端冲动的美国制度特征,如今却被用来巩固权力。一旦这座堡垒被曾经抵御的力量占据,其防御工事便可能变成陷阱。
第二届特朗普政府大幅扩张了总统权力。白宫试图篡夺国会的部分财政支出权,并重新划分公务员类别,以便总统更容易解雇他们。特朗普在加利福尼亚州部署了国民警卫队,尽管州长反对,但以应对“叛乱”为名义进行。
尽管法院多次驳斥政府,但其权力也正受到挑战:政府加大了对法官的言辞攻击,并被指控拖延执行法院命令。学生被拘留,甚至有因撰写评论文章而被拘留的案例。如今,我们处于这样一种局面,民主领域的顶尖学者更加明确地表示,美国在向专制滑落的过程中,已经越过了重要(尽管可逆)的界限。
 6 月 23 日,在洛杉矶针对移民突袭的近期抗议活动后,国民警卫队武装成员驻守现场。摄影师:Frederic J. Brown/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6 月 23 日,在洛杉矶针对移民突袭的近期抗议活动后,国民警卫队武装成员驻守现场。摄影师:Frederic J. Brown/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几年前,鲜有人会认为这可能实现。尽管存在本土的威权势力——尤以吉姆·克劳法时期的南方为甚——但从国家层面来看,美国拥有数百年稳定运作的民主制度,至少在满足民主的最低标准方面表现突出:我们举行竞争性、自由的选举,执政党可能败选并接受结果。
当前面临威胁的体制曾经历过极为严峻的考验,包括一场极其血腥的内战和尼克松白宫的权力夺取。然而,民主通过应对这些挑战得以存续和发展:扩大了选举权;将官僚体系从“战利品”制度转变为更专业的公务员制度;并采取了一系列立法措施以防止再次发生水门事件。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记录使人们形成了一种可以理解且几乎不可动摇的信念,认为美国民主受到牢不可破的制度保护。正如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在被问及 2016 年时任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可能对民主构成的威胁时所说:“我们不是罗马尼亚。”
无论 2016 年的情况如何,如今这种信心显得不明智。根据一项调查,自特朗普再次就任以来,政治学家对美国民主的评价显著下降。换句话说,这一次可能真的不同了。
两党陷阱
在美国大部分历史时期,两党制一直是防止政治极端势力或反民主力量崛起的屏障。政治学家将此归因于所谓的“中间选民定理”:如果其中一党偏离中间立场,另一党便能吸引足够的中间选民支持,从而赢得选举。
在美国,政治家通过获得最多选票(相对多数)获胜,这与按得票比例分配议席的比例代表制形成对比。比例代表制在欧洲大陆较为普遍,对小党派更为友好,使它们能够将代表权转化为实际的政治影响力——通常通过在组建执政联盟中发挥关键作用,并以此换取政策让步。
通过使第三方(或第四、第五方)难以赢得席位,美国的两党制在很大程度上孕育了温和派,即使在地方层面也是如此。两大政党也异常长寿,人们认为这为政治提供了另一种连续性和稳定性。政党能够比个人或昙花一现的运动拥有更长远的时间视角。这强化了民主契约的一个关键部分,即选举失败者必须同意和平地将权力交给胜利者。只有在未来有真正机会重新执政时,这种做法才有意义。在美国的两党制中,失败者可以对自己很快再次获胜充满信心。
在某种程度上,中位选民模型及其所带来的影响本身就是其时代的产物。经济学家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在 1957 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了这一基本观点,当时的政治氛围极为温和,以至于美国政治学会在 1950 年的一份报告中呼吁增加党派间的分歧,以便选民能够更清楚地区分各政党。
但唐斯及其同时代的人很少考虑如果他们的逻辑失效会发生什么。即使有 1950 年代纯粹的政治理论,如果极端主义或反民主势力设法掌控了两大政党之一,会怎样?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两党制将不再是遏制极端主义的屏障,反而会成为助推器。它会将极端分子推向一个非常强势的选举地位,远比在按比例代表制下由小党派代表时更为显著。
尽管特朗普在某些议题上持有温和立场(例如承诺不削减医疗保险或社会保障),这或许为他赢得了一部分选民的支持,但他在 2016 年获得共和党提名时,仅获得不到 50%的初选选民支持。即使是他的初选总票数,也高估了他在党内的初始支持度,因为在锁定提名后,他的支持率才显著提升。根据 YouGov 2025 年 5 月的民调,只有 16%的美国成年人认同 MAGA 共和党人。然而,特朗普和 MAGA 无疑已经掌控了共和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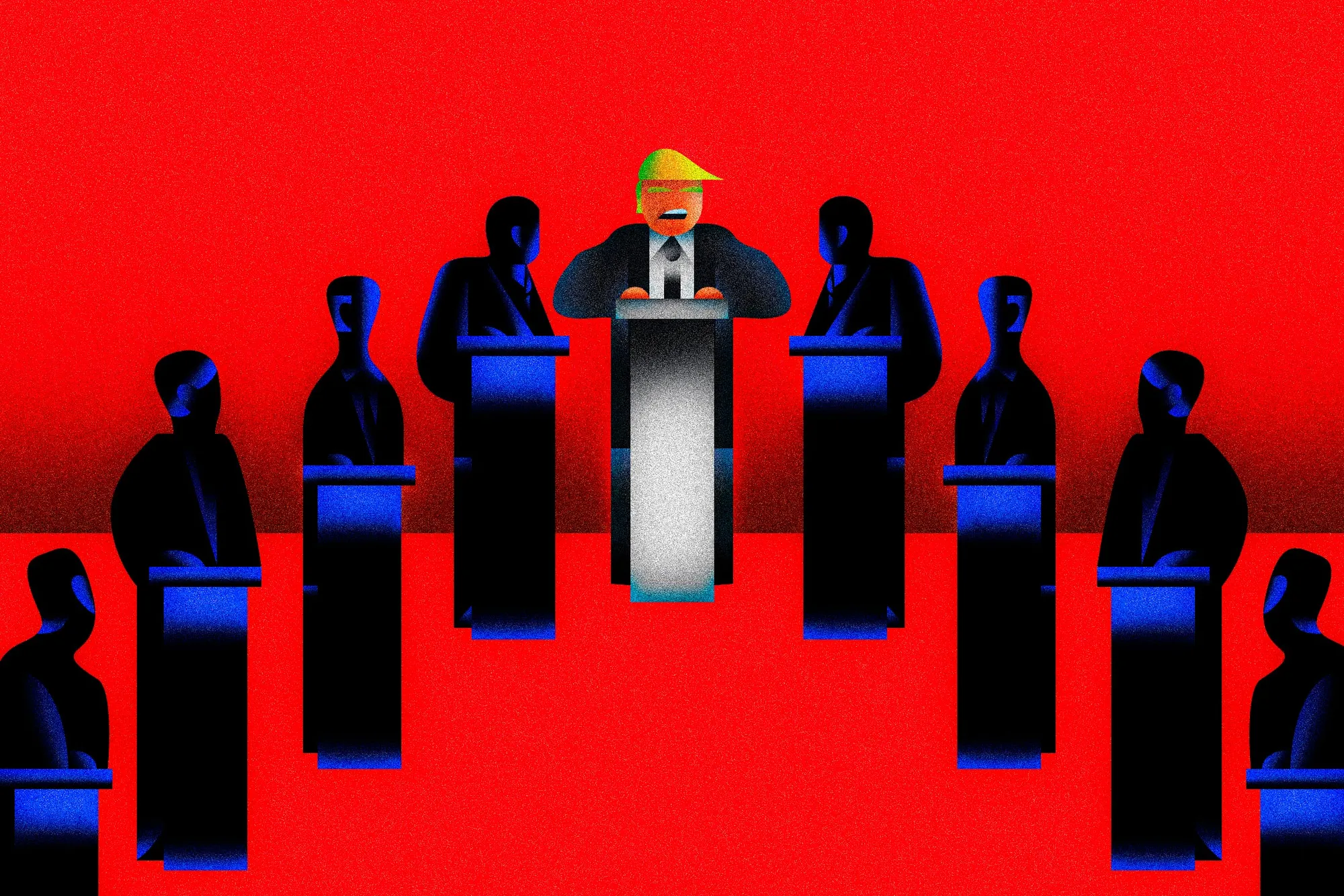 插图:Derek Abella,彭博社
插图:Derek Abella,彭博社
是什么让 MAGA 派系能够做到这一点?答案始于几十年来逐渐发生的选民党派分化和极化。早在 1990 年代末,极化已经变得如此严重,以至于政治学家莫里斯·菲奥里纳写了一篇文章,质疑“中间选民到底去哪儿了?”这种分裂加剧的原因无疑有很多:有人归咎于社交媒体,有人指责福克斯新闻或纽特·金里奇。不管原因是什么,极端的党派立场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每个党派的大多数选民都会支持任何候选人,无论多么糟糕,只要那是他们党派的候选人。
其次,尽管选民对政党保持忠诚,但如今的“空心党”(借用政治学家丹尼尔·施洛兹曼和萨姆·罗森费尔德创造的术语)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对候选人遴选过程拥有严格控制。过去在烟雾弥漫的密室和经纪人大会时代,政党对候选人的掌控力远远强于现在。(1968 年时,时任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甚至未参加任何初选,就赢得了民主党提名。)
开放初选制度——允许注册选民,包括那些有时甚至未加入该党派的人参与投票——使特朗普得以策划被称为“敌意接管”的共和党控制权转移。而党派忠诚则使他在 2016 年和 2024 年两度当选总统。
与中间选民定理的原始逻辑相反,美国的两党制——加上空洞的政党结构和尖锐的极化——如今成了极端主义的温床。如今特朗普稳坐白宫,两党制放大了他的权力:他和他的忠实代理人能够可信地威胁每一位共和党当选官员,摧毁他们的政治生涯。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他们有权剥夺这些政治人物的“R”标签,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没有这个标签,他们在选举中注定失败。
这与巴西的情况大不相同。巴西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的支持者曾试图发动类似 1 月 6 日的暴乱。博索纳罗否认参与及任何不当行为,但他被禁止担任公职八年,且面临入狱的现实可能。
巴西为何会有这种差异?巴西采用“开放名单”选举制度,各州的议席分配依据候选人获得的个人票数。此外,政治家在竞选时有多种选择:2022 年,至少有 23 个不同政党在众议院(巴西版的众议院)中当选议员。因此,博索纳罗在近四十年的政治生涯中曾加入过九个不同政党,他从未拥有威胁其支持基础内政治家的权力。政治家们可以简单地转换政党,并带走他们的选票。结果,他对立法者的影响力一直较低。
 前巴西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于六月在圣保罗的一场集会上。摄影师:米格尔·辛卡里奥尔/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前巴西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于六月在圣保罗的一场集会上。摄影师:米格尔·辛卡里奥尔/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非自由主义的实验场
不仅仅是两党制从支柱变成了累赘。与大多数国家不同,美国联邦选举的组织和计票完全是分散进行的。这通常是防止破坏自由公平选举的有力屏障,因为它使得通过控制单一中央选举机构来实施大规模舞弊变得更加困难。
然而,正如两党制一样,这种地方控制如今与党派倾向的上升产生了令人担忧的互动,反而使得偏向某一党派的局面更容易形成。
如果你试图操纵美国总统选举,大多数州都不值得费心。佛蒙特州在选举之夜肯定会投给民主党,而阿拉巴马州则会投给共和党。只有少数几个摇摆州和邻近摇摆的州才会产生关键影响,而这些战场州的胜负可能只差几百票。(德克萨斯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两党都有竞争力,选举人团制度几乎注定会导致选举结果悬而未决。)
只需在关键州安插几名立场坚定的党派官员,就足以扭转一场接近且分散的选举结果。如果你觉得在佐治亚州这样的地方篡改选举难以想象,别忘了特朗普在 2020 年就曾试图这么做。虽然当时国务卿坚守立场,但未来如果换成更忠诚的党派基层人员,情况完全可能会更容易被操控。
在一些摇摆州,已经实施或提议采取一些较为温和的操控手段,比如要求提供带照片的身份证明和削减提前投票时间。因此,虽然分散式选举能够防范某些类型的漏洞,但也会带来其他通常在别处不存在的问题。
在这两种情况下,从强势转为弱势的根源都在于政治极化的加剧。两党曾使政治趋于温和,直到意识形态的分化和选民对对立党的厌恶加深,将双方推向极端——而政党则利用并放大了这种极端化。州和地方对选举的控制曾使得在多个州竞争激烈时干预选举变得困难。但当选举的胜负取决于少数几个战场州,而这些州的选举由党派官员掌控时,干预选举看起来相对容易。
我们担心,许多人视为抵御专制的终极屏障——美国宪法——也可能面临类似的情况。潜在的独裁者常常试图修改宪法,而美国之所以受益,正是因为其宪法难以修改。然而,这种观点忽视了一个事实:许多其他国家通过宪法修正案实现的变革,在美国则是通过最高法院的判决来完成的。
仅以最近的一个例子来说,2024 年法院裁定总统对“官方行为”享有绝对的刑事豁免权。这种保护在宪法文本中并无体现——宪法简洁且灵活,因此始终开放解读。美国的宪政体制依赖于少数身披法袍的法律权威的意见,而他们显然也难以避免日益加剧的党派倾向。
美国的政治制度使民主得以繁荣发展了几个世纪。但我们当前所经历的真实威胁威权主义的局面,应促使我们思考如何减少其再次发生的可能性。完全废除分散的选举制度、共和党和民主党,或解散最高法院,既不可行也不理想。相反,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及时调整这些机构——以及它们所处的高度极化的环境——以稳定美国的民主。
菲利普·坎潘特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彭博杰出教授。雷·菲斯曼是波士顿大学斯莱特家族行为经济学教授。
